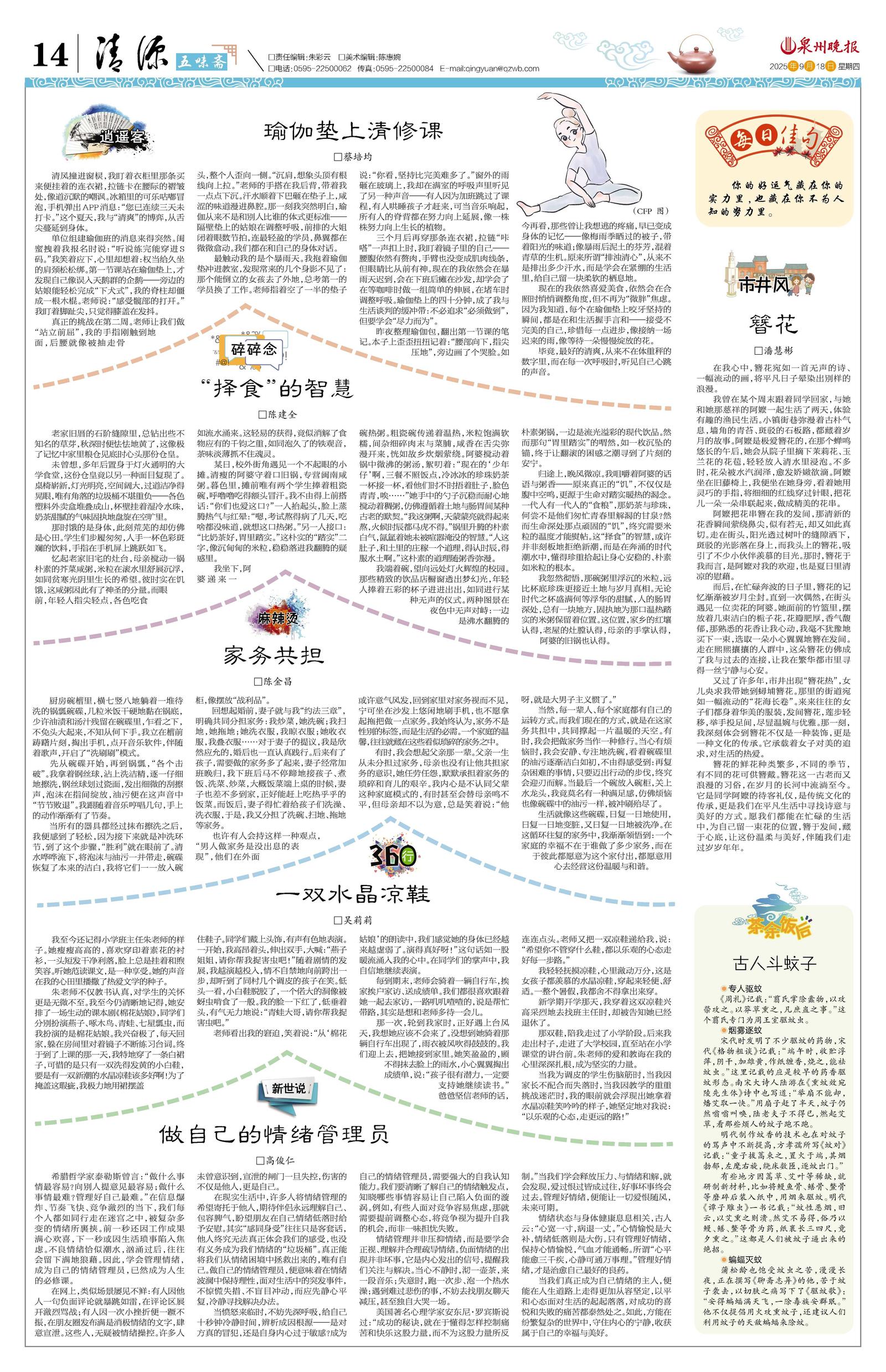老家旧厝的石阶缝隙里,总钻出些不知名的草芽,秋深时便怯怯地黄了,这像极了记忆中家里粮仓见底时心头那份仓皇。
未曾想,多年后置身于灯火通明的大学食堂,这份仓皇竟以另一种面目复现了。桌椅崭新,灯光明亮,空间阔大,过道洁净得晃眼,唯有角落的垃圾桶不堪重负——各色塑料外卖盒堆叠成山,杯壁挂着湿冷水珠,奶茶甜腻的气味固执地盘旋在空旷里。
那时饿的是身体,此刻荒芜的却仿佛是心田。学生们步履匆匆,人手一杯色彩斑斓的饮料,手指在手机屏上跳跃如飞。
忆起老家旧宅的灶台,母亲搅动一锅朴素的芥菜咸粥,米粒在滚水里舒展沉浮,如同贫寒光阴里生长的希望。彼时实在饥饿,这咸粥因此有了神圣的分量。而眼前,年轻人指尖轻点,各色吃食如流水涌来。这轻易的获得,竟似消解了食物应有的千钧之重,如同泡久了的铁观音,茶味淡薄抓不住魂灵。
某日,校外街角遇见一个不起眼的小摊。清瘦的阿婆守着口旧锅,专营闽南咸粥。暮色里,摊前唯有两个学生捧着粗瓷碗,呼噜噜吃得额头冒汗。我不由得上前搭话:“你们也爱这口?”一人抬起头,脸上蒸腾热气与红晕:“嗯,考试熬得病了几天,吃啥都没味道,就想这口热粥。”另一人接口:“比奶茶好,胃里踏实。”这朴实的“踏实”二字,像沉甸甸的米粒,稳稳落进我翻腾的疑惑里。
我坐下,阿婆递来一碗热粥。粗瓷碗传递着温热,米粒饱满软糯,间杂细碎肉末与菜脯,咸香在舌尖弥漫开来,恍如故乡炊烟萦绕。阿婆搅动着锅中微沸的粥汤,絮叨着:“现在的‘少年仔’啊,三餐不照饭点,冷冰冰的珍珠奶茶一杯接一杯,看他们时不时捂着肚子,脸色青青,唉……”她手中的勺子沉稳而耐心地搅动着稠粥,仿佛遵循着土地与肠胃间某种古老的默契。“我这粥啊,天蒙蒙亮就得起来熬,火候时辰都马虎不得。”锅里升腾的朴素白气,氤氲着她未被喧嚣淹没的智慧。“人这肚子,和土里的庄稼一个道理,得认时辰,得服水土啊。”这朴素的道理随粥香弥漫。
我端着碗,望向远处灯火辉煌的校园。那些精致的饮品店橱窗透出梦幻光,年轻人捧着五彩的杯子进进出出,如同进行某种无声的仪式。两种图景在夜色中无声对峙:一边是沸水翻腾的朴素粥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现代饮品。然而那句“胃里踏实”的喟然,如一枚沉坠的锚,终于让翻滚的困惑之潮寻到了片刻的安宁。
归途上,晚风微凉。我咀嚼着阿婆的话语与粥香——原来真正的“饥”,不仅仅是腹中空鸣,更源于生命对踏实暖热的渴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食粮”,那奶茶与珍珠,何尝不是他们匆忙青春里解渴的甘泉?然而生命深处那点顽固的“饥”,终究需要米粒的温度才能熨帖。这“择食”的智慧,或许并非刻板地拒绝新潮,而是在奔涌的时代潮水中,懂得珍重拾起让身心安稳的、朴素如米粒的根本。
我忽然彻悟,那碗粥里浮沉的米粒,远比杯底珍珠更接近土地与岁月真相。无论时代之杯盛满何等浮华的甜腻,人的肠胃深处,总有一块地方,固执地为那口温热踏实的米粥保留着位置。这位置,家乡的红壤认得,老屋的灶膛认得,母亲的手掌认得,阿婆的旧锅也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