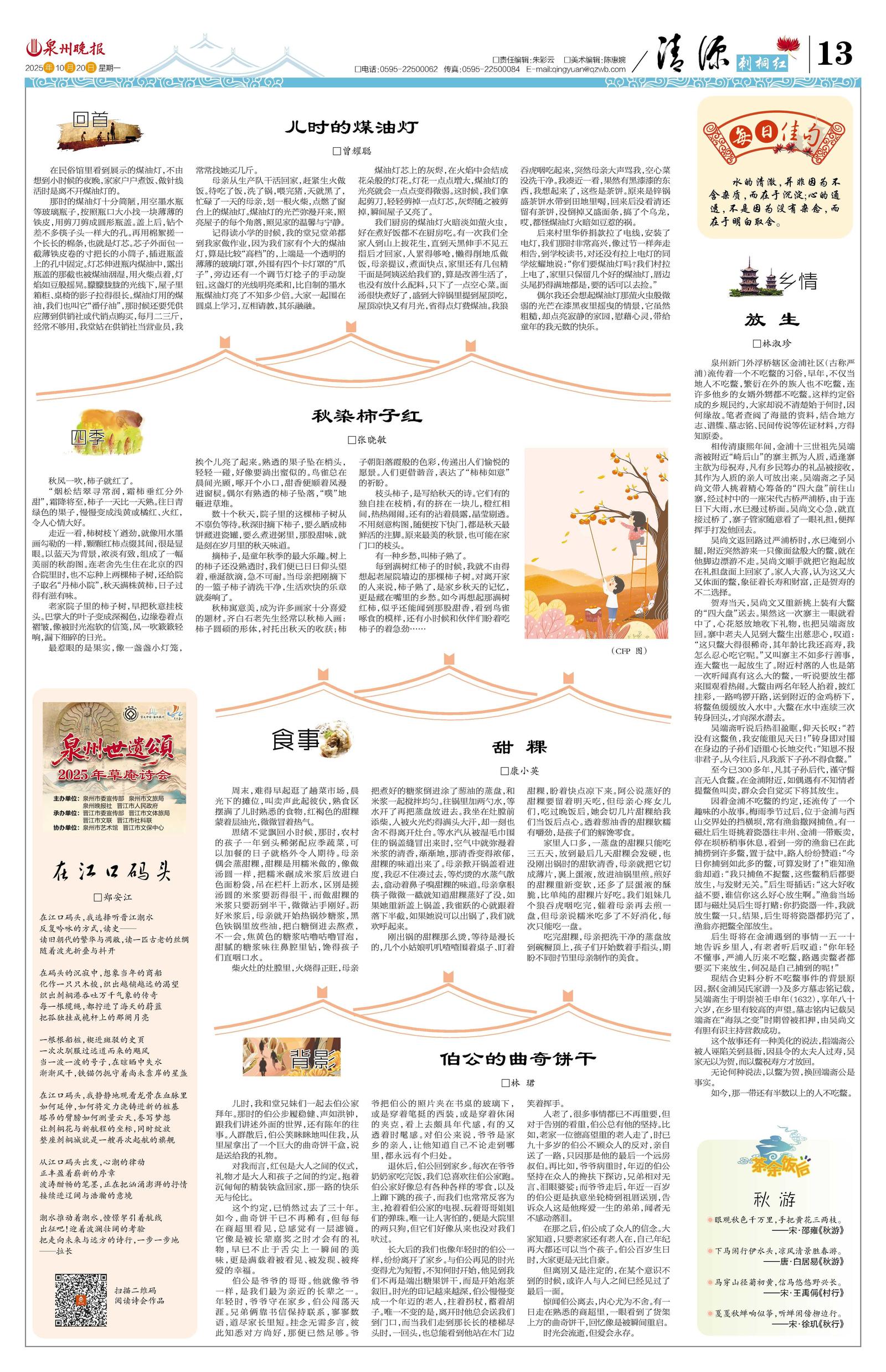在民俗馆里看到展示的煤油灯,不由想到小时候的夜晚,家家户户煮饭、做针线活时是离不开煤油灯的。
那时的煤油灯十分简陋,用空墨水瓶等玻璃瓶子,按照瓶口大小找一块薄薄的铁皮,用剪刀剪成圆形瓶盖。盖上后,钻个差不多筷子头一样大的孔。再用棉絮搓一个长长的棉条,也就是灯芯。芯子外面包一截薄铁皮卷的寸把长的小筒子,插进瓶盖上的孔中固定。灯芯伸进瓶内煤油中,露出瓶盖的那截也被煤油洇湿,用火柴点着,灯焰如豆般摇晃。朦朦胧胧的光线下,屋子里箱柜、桌椅的影子拉得很长。煤油灯用的煤油,我们也叫它“番仔油”,那时候还要凭供应簿到供销社或代销点购买,每月二三斤,经常不够用,我堂姑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我常常找她买几斤。
母亲从生产队干活回家,赶紧生火做饭。待吃了饭,洗了锅,喂完猪,天就黑了,忙碌了一天的母亲,划一根火柴,点燃了窗台上的煤油灯。煤油灯的光芒弥漫开来,照亮屋子的每个角落,照见家的温馨与宁静。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堂兄堂弟都到我家做作业,因为我们家有个大的煤油灯,算是比较“高档”的,上端是一个透明的薄薄的玻璃灯罩,外围有四个卡灯罩的“爪子”,旁边还有一个调节灯捻子的手动旋钮。这盏灯的光线明亮柔和,比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亮了不知多少倍。大家一起围在圆桌上学习,互相请教,其乐融融。
煤油灯芯上的灰烬,在火焰中会结成花朵般的灯花。灯花一点点增大,煤油灯的光亮就会一点点变得微弱。这时候,我们拿起剪刀,轻轻剪掉一点灯芯,灰烬随之被剪掉,瞬间屋子又亮了。
我们厨房的煤油灯火暗淡如萤火虫,好在煮好饭都不在厨房吃。有一次我们全家人到山上拔花生,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后才回家,人累得够呛,懒得削地瓜做饭,母亲提议,煮面快点,家里还有几包精干面是阿姨送给我们的,算是改善生活了,也没有放什么配料,只下了一点空心菜。面汤很快煮好了,盛到大锌锅里提到屋顶吃,屋顶凉快又有月光,省得点灯费煤油。我狼吞虎咽吃起来,突然母亲大声骂我,空心菜没洗干净。我凑近一看,果然有黑漆漆的东西,我想起来了,这些是茶饼。原来是锌锅盛茶饼水带到田地里喝,回来后没看清还留有茶饼,没倒掉又盛面条,搞了个乌龙,哎,都怪煤油灯火暗如豆惹的祸。
后来村里华侨捐款拉了电线,安装了电灯,我们那时非常高兴,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到学校读书,对还没有拉上电灯的同学炫耀地说:“你们要煤油灯吗?我们村拉上电了,家里只保留几个好的煤油灯,厝边头尾扔得满地都是,要的话可以去捡。”
偶尔我还会想起煤油灯那萤火虫般微弱的光芒在漆黑夜里摇曳的情景,它虽然粗糙,却点亮寂静的家园,慰藉心灵,带给童年的我无数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