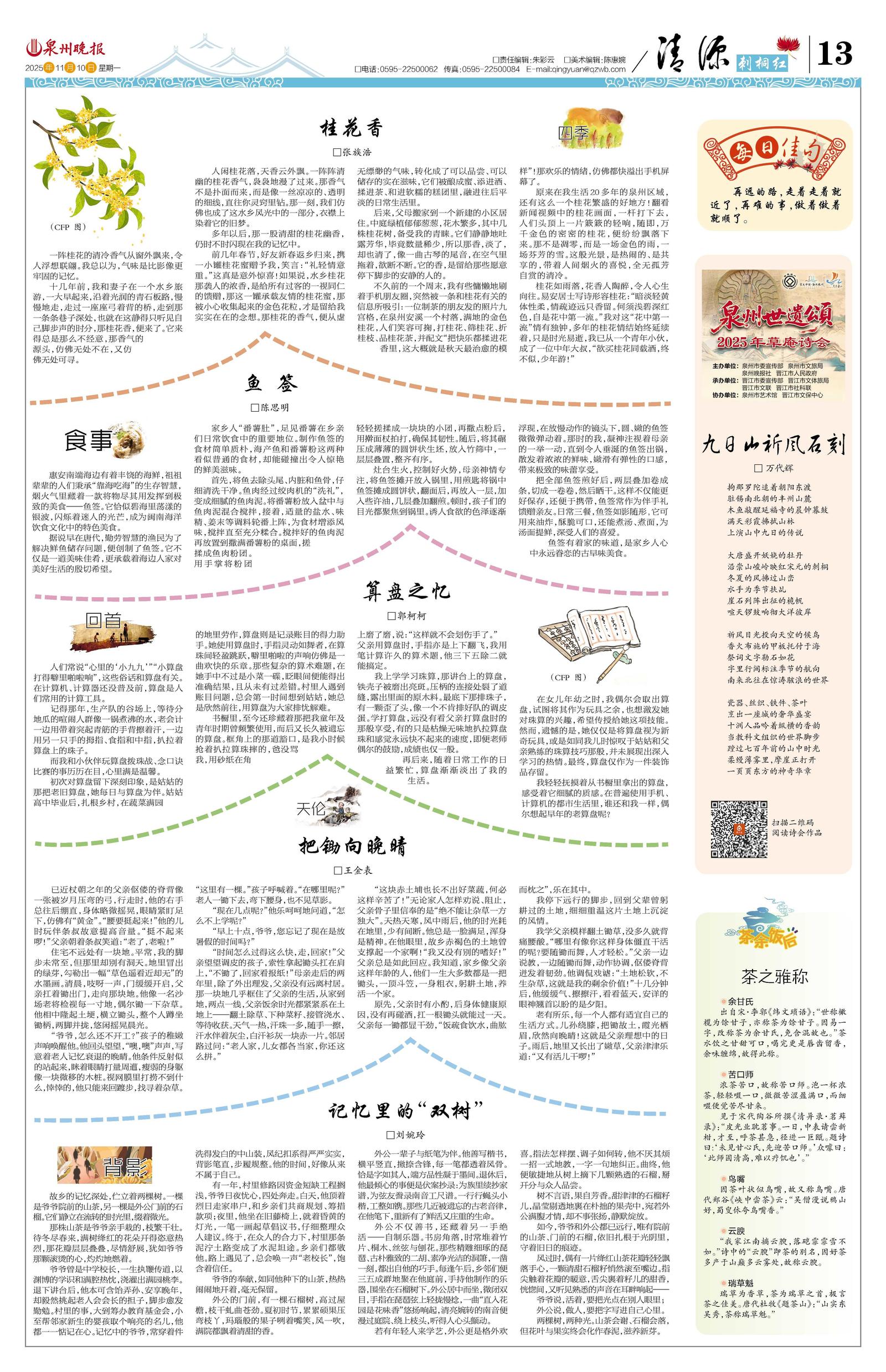故乡的记忆深处,伫立着两棵树。一棵是爷爷院前的山茶,另一棵是外公门前的石榴。它们静立在流转的时光里,缀着微光。
那株山茶是爷爷亲手栽的,枝繁干壮。待冬尽春来,满树绛红的花朵开得恣意热烈,那花瓣层层叠叠,尽情舒展,犹如爷爷那颗滚烫的心,灼灼地燃着。
爷爷曾是中学校长,一生执鞭传道,以渊博的学识和满腔热忱,浇灌出满园桃李。退下讲台后,他本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却毅然挑起老人会会长的担子,脚步愈发勤勉。村里的事,大到筹办教育基金会,小至帮邻家新生的婴孩取个响亮的名儿,他都一一惦记在心。记忆中的爷爷,常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背影笔直,步履规整。他的时间,好像从来不属于自己。
有一年,村里修路因资金短缺工程搁浅,爷爷日夜忧心,四处奔走。白天,他顶着烈日走家串户,和乡亲们共商规划、筹措款项;夜里,他坐在旧藤椅上,就着昏黄的灯光,一笔一画起草倡议书,仔细整理众人建议。终于,在众人的合力下,村里那条泥泞土路变成了水泥坦途。乡亲们都敬他。路上遇见了,总会唤一声“老校长”,饱含着信任。
爷爷的奉献,如同他种下的山茶,热热闹闹地开着,毫无保留。
外公的门前,有一棵石榴树,高过屋檐,枝干虬曲苍劲。夏初时节,累累硕果压弯枝丫,玛瑙般的果子咧着嘴笑,风一吹,满院都飘着清甜的香。
外公一辈子与纸笔为伴。他善写楷书,横平竖直,撇捺含锋,每一笔都透着风骨。恰是字如其人,端方品性凝于墨间。退休后,他最倾心的事便是伏案抄录:为族里续抄家谱,为弦友誊录南音工尺谱。一行行蝇头小楷,工整如镌。那些几近被遗忘的古老音律,在他笔下,重新有了鲜活又庄重的生命。
外公不仅善书,还藏着另一手绝活——自制乐器。书房角落,时常堆着竹片、桐木、丝弦与刨花。那些精雕细琢的琵琶、古朴雅致的二胡、素净光洁的洞箫,一凿一刻,都出自他的巧手。每逢午后,乡邻们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他庭前,手持他制作的乐器,围坐在石榴树下。外公居中而坐,微闭双目,手指在琵琶弦上轻拢慢捻,一曲“直入花园是花味香”悠扬响起,清亮婉转的南音便漫过庭院、绕上枝头,听得人心头颤动。
若有年轻人来学艺,外公更是格外欢喜。指法怎样摆、调子如何转,他不厌其烦一招一式地教,一字一句地纠正。曲终,他便敏捷地从树上摘下几颗熟透的石榴,掰开分与众人品尝。
树不言语,果自芳香。甜津津的石榴籽儿,晶莹剔透地裹在朴拙的果壳中,宛若外公满腹才情,却不事张扬,静默绽放。
如今,爷爷和外公都已远行,唯有院前的山茶、门前的石榴,依旧扎根于光阴里,守着旧日的痕迹。
风过时,偶有一片绛红山茶花瓣轻轻飘落手心,一颗清甜石榴籽悄然滚至嘴边。指尖触着花瓣的暖意,舌尖裹着籽儿的甜香,恍惚间,又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爷爷说,活着,要把光点在别人眼里;
外公说,做人,要把字写进自己心里。
两棵树,两种光。山茶会谢、石榴会落,但花叶与果实终会化作春泥,滋养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