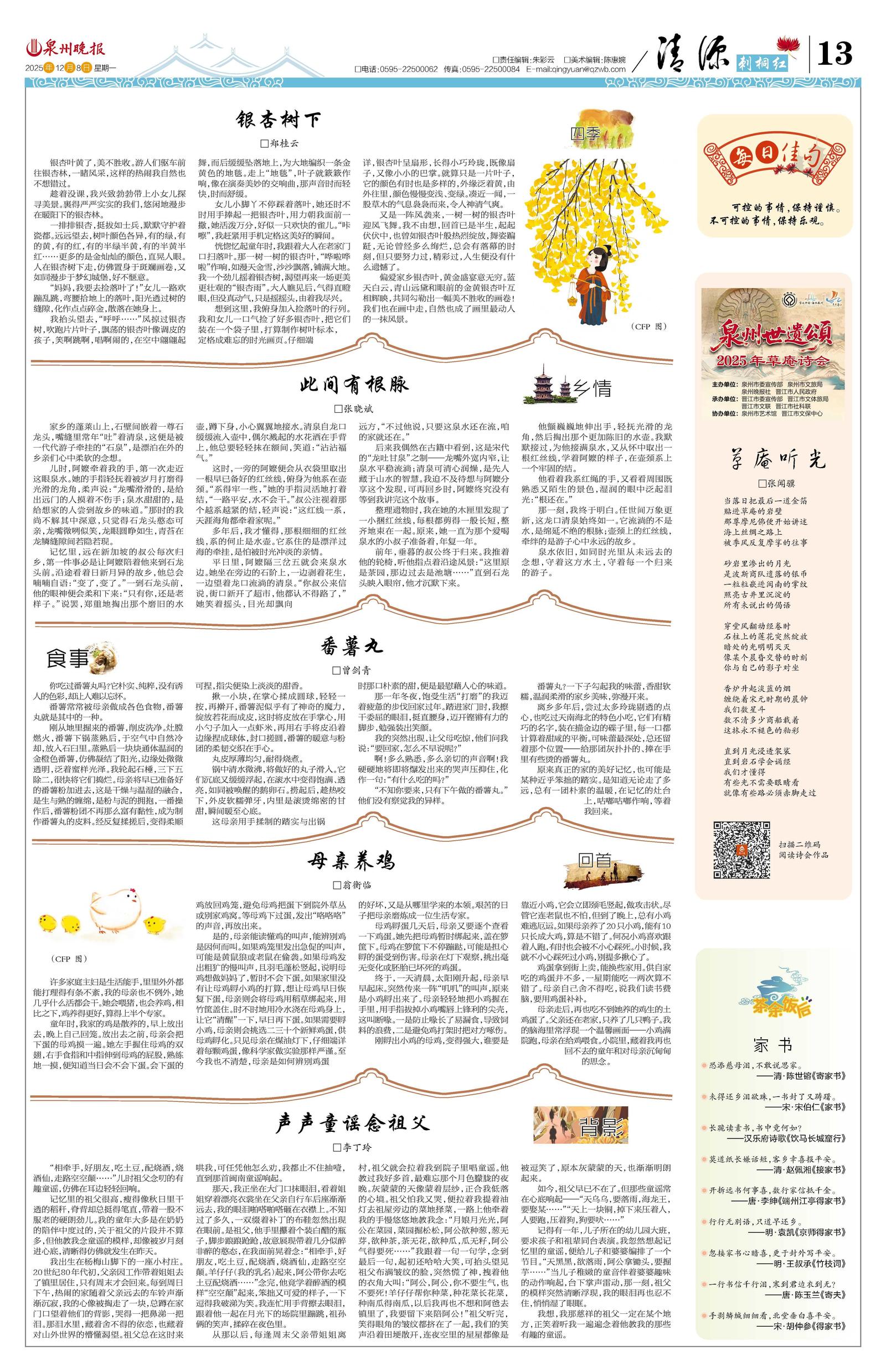□曾剑青
你吃过番薯丸吗?它朴实、纯粹,没有诱人的色彩,却让人难以忘怀。
番薯常常被母亲做成各色食物,番薯丸就是其中的一种。
刚从地里掘来的番薯,削皮洗净。灶膛燃火,番薯下锅蒸熟后,于空气中自然冷却,放入石臼里。蒸熟后一块块通体温润的金橙色番薯,仿佛凝结了阳光,边缘处微微透明,泛着蜜样光泽。我轮起石棰,三下五除二,很快将它们捣烂。母亲将早已准备好的番薯粉加进去,这是干燥与温湿的融合,是生与熟的缠绵,是粉与泥的拥抱,一番操作后,番薯粉团不再那么富有黏性,成为制作番薯丸的皮料。经反复揉搓后,变得柔顺可捏,指尖便染上淡淡的甜香。
揪一小块,在掌心揉成圆球,轻轻一按,再擀开,番薯泥似乎有了神奇的魔力,绽放若花而成皮,这时将皮放在手掌心,用小勺子加入一点虾米,再用右手将皮沿着边缘捏成球体,封口搓圆,番薯的暖意与粉团的柔韧交织在手心。
丸皮厚薄均匀,耐得烧煮。
锅中清水微沸,将做好的丸子滑入。它们沉底又缓缓浮起,在滚水中变得饱满、透亮,如同被唤醒的鹅卵石。捞起后,趁热咬下,外皮软糯弹牙,内里是滚烫绵密的甘甜,瞬间暖至心底。
这母亲用手揉制的踏实与出锅时那口朴素的甜,便是最慰藉人心的味道。
那一年冬夜,饱受生活“打磨”的我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过年。踏进家门时,我擦干委屈的眼泪,挺直腰身,迈开铿锵有力的脚步,勉强装出笑颜。
我的突然出现,让父母吃惊,他们问我说:“要回家,怎么不早说呢?”
啊!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声音啊!我硬硬地将即将爆发出来的哭声压抑住,化作一句:“有什么吃的吗?”
“不知你要来,只有下午做的番薯丸。”他们没有察觉我的异样。
番薯丸?一下子勾起我的味蕾,香甜软糯,温润柔滑的家乡美味,弥漫开来。
离乡多年后,尝过太多玲珑剔透的点心,也吃过天南海北的特色小吃,它们有精巧的名字,装在描金边的碟子里,每一口都计算着甜咸的平衡。可味蕾最深处,总还留着那个位置——给那团灰扑扑的、捧在手里有些烫的番薯丸。
原来真正的家的美好记忆,也可能是某种近乎笨拙的踏实。是知道无论走了多远,总有一团朴素的温暖,在记忆的灶台上,咕嘟咕嘟作响,等着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