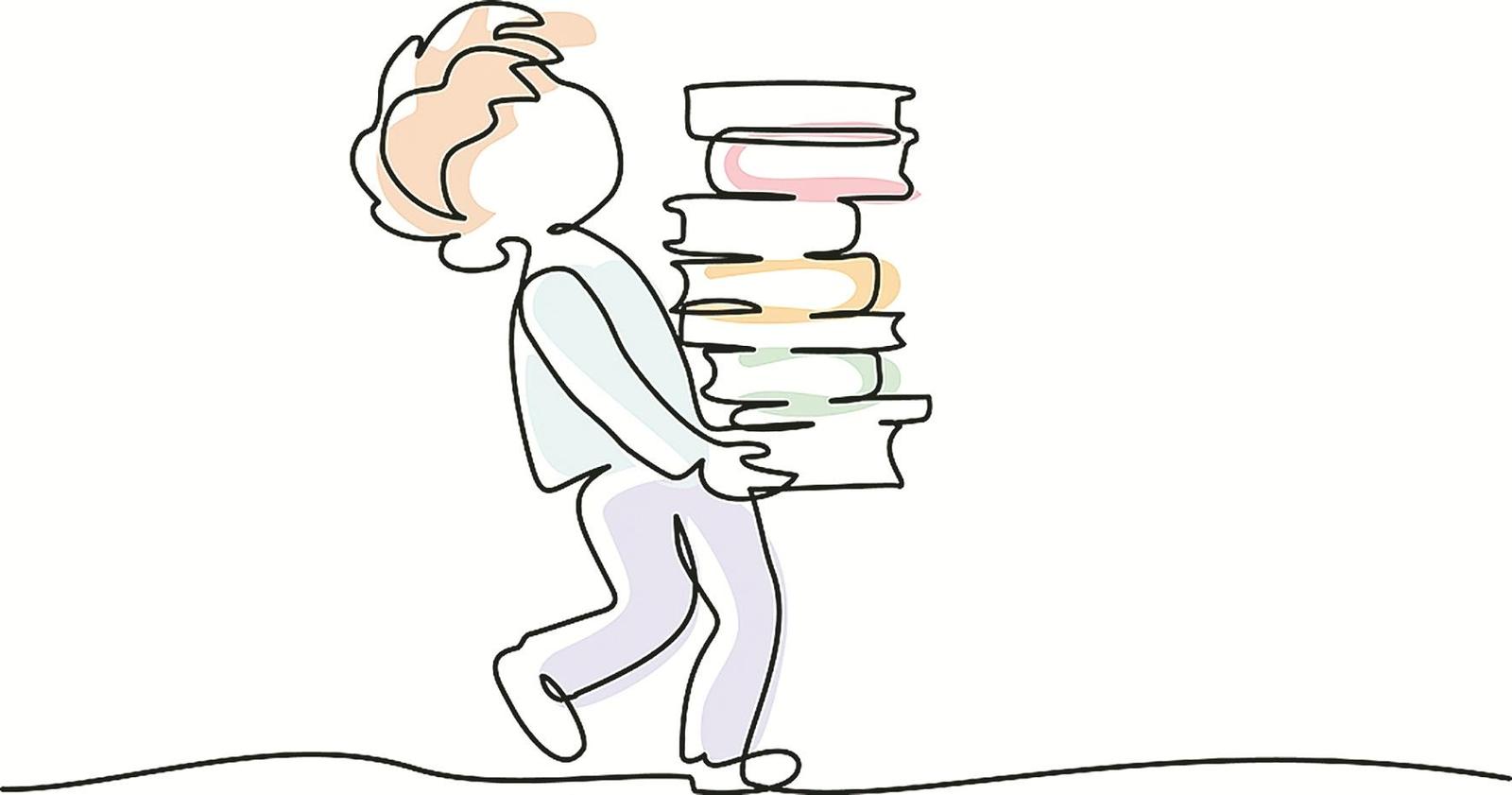小时候,老家通光通风的,是一扇小木窗。屋里除了父母结婚时那口褪了大红漆的老柜子,再寻不着像样的家具。我的书,便也没了去处,只能一摞摞地堆在吱呀作响的桌角,或是几本最常翻的,蜷在枕边。那时,我心底便埋下了一个沉甸甸的奢望——何时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柜,让我的书,也能有个安稳的家?
书无处安放的童年,阅读的来源也同样拮据。一位要好的同学来自书香门第,家中有整整一面墙的书柜,《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摆满了架子。那是我第一次窥见“坐拥书城”的景象,每次去蹭书,都像赴一场盛宴,翻书前,我都会小心翼翼洗净擦干双手,生怕弄脏同学的宝贝书籍。那时,最豪横的阅读记忆,属于街道地摊上出租的“小人书”,一分钱一本,不限时间,反复翻阅,可以过足书瘾。
高中时代,父母亲在鳌峰脚下建了石头房子。一层的石头房分几次、历经多年才建成,家里也没添置几件像样的家具,自然更不会有心心念念的书柜。搬到石头房居住很多年,我的书依旧无处安置。
参加工作多年后,我终于在宿舍购置了第一个书柜,一大堆书也总算暂时有了落脚之地。有了小孩后,许是周岁时便开始教他咿呀诵读唐诗的缘故,他竟也成了个十足的“小书迷”。爱书如命的孩子把零花钱都花在买书上,书架很快不堪重负,书桌也成了权宜的“书柜”。直到去年搬到新居,爱人在大厅定制了一个左右两格、上下七层的巨大书柜——我想,这回书总算能有个安稳的归宿了。
于是,我开始了真正的“驮书”之旅。像一只固执的蚂蚁,我每日下班后从宿舍步行六公里至新居,背包里沉甸甸地装着一部分书,将它们分类整理,请上书架。爱人调侃:何不开车一次性运完?她或许不明白,这并非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更像是一场郑重的仪式。
然而,我很快发现,纵使是如此大体量的书柜,也很快被各类文学、文史专著及期刊填满。我不得不打起新居卧室里低柜的主意……爱人低声埋怨着:带回那么多书,没地方放啊!此时,我想起一位爱书的好友,他的几万册图书堆满了老家临街的两套房,不禁慨叹:藏书容易堆书难啊!但这幸福的烦恼,或许正是爱书之人的宿命。
在爱人的一再提醒和督促下,驮完书的我,开始了艰难的藏书处理工程。分门别类时,指尖抚过每一本书的封面,如同与旧友作别。优先保存的是那些留有作者亲笔签名、弥足珍贵的原著;而那些重复的书籍,或版本不同,或装帧各异,我从中遴选出最旧的一本留作纪念,其余的郑重转赠给同样爱书的朋友。一本早年的《三毛流浪记》,书页已泛黄脆裂,我用透明胶细心粘好修补,毫不犹豫留下,因为那是我花第一个月四分之一工资所买的书。一些不常翻阅、没有书号的书籍,虽曾在某个深夜偶尔翻阅,如今也只能轻轻堆叠,准备请出书柜。不舍得的还有那些参考价值有限的内部刊物,纸张早已泛黄,记载着某个时期的印记,我反复摩挲,终究还是驮出去,轻轻放入垃圾桶——仿佛亲手掩埋一段时光。
儿子如今已在省城工作数年,每次视频通话,他总喜欢把镜头转向租住房子内自己的书架,向我展示他最近又新购的书籍。镜头里,他的书架已经延伸到墙角、窗台,甚至床底下的收纳箱里。没想到这爱书的基因,竟也遗传得如此彻底。
新居的夜晚格外宁静,唯有书香在灯下无声弥漫。周末,儿子回到新居,看他安然地在满满的书架前阅览,我总会想起当年那个枕边蜷着几本书、奢望着一个书柜的男孩。这沉甸甸的驮书之路,我从一方陋室走到了今天,而他,正从今天走向更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