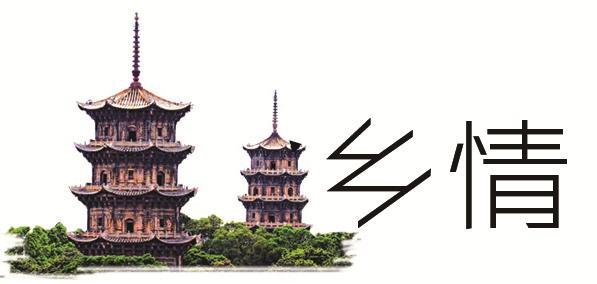□郑真杰
我的老家是泉州靠海的一座小村庄,每次推开自家窗户,总能与海风“撞个满怀”。平时站在屋外远眺,先入眼的是一片紫菜田,紫褐色的藻体在潮水中轻轻摇曳,退潮时,竹竿与绳索才会显露出来,横七竖八地插在滩涂上,如同大地生出的胡须。稍远处还有一座小岛,它被本地人称为“鲎屿”,因为从远处看那里仿佛一只搁浅的鲎。
鲎屿上有一座石头厝,如今灰黑色的墙壁布满盐霜,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犹如鲎壳上的纹路。那屋子原是村里渔民们养殖海蛎、海带、紫菜的憩息点,后来渔民们使用玻璃钢船和机械吊机养殖海产,不再需要上岛干活,鲎屿上的石头厝才渐渐无人来落脚。不过听伯父说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乡亲会在渔船修补的季节,趁着大潮汛的最低潮,结伴泅水去鲎屿上钓鱼,以贴补家用,待到潮水退至极限,再带着钓到的鱼,凫水回岸。当时的石头厝还完好,来钓鱼的乡亲们便将它当做临时的歇脚处,一用又是多年。
现今石头厝已经变得破败,窗台仅剩几根横梁支撑着,远观好像鲎蜕下的残甲。厝前的空地还散落着几个锈蚀的铁桶和断裂的竹筐,想必是过去用来盛放海产的容器。唯一不变的是每到夏夜,鲎仍会爬到岛上的沙滩产卵,与石头厝相伴一段时间。我平时喜欢在清晨或黄昏去海边散步,顺便远眺鲎屿。靠近岛屿的海中网箱连绵不绝,它们随波浪上下浮动,远看好像一群起舞的水鸟。若有渔民抬手抛撒饲料,网箱里定会翻腾起银色的浪花,那也是鱼群争食发出的动静。海鸥们精明得很,这时定会在网箱附近低翔,伺机抢夺鱼儿的口粮。
老家沙滩的沙粒极细,赤脚踩上去,先是觉得绵软,继而才有几分刺痛袭来。沙滩附近的礁石很有野趣,一块块黑黢黢的石头,经年累月受海水冲刷,有的形状圆润如卧水的海豹,有的样子嶙峋如蛰伏的巨兽。礁石上满是海蛎壳的残骸,仔细看还有渔民采贝留下的道道凿痕。我曾在礁石缝中发现了半块陶碗碎片,它的边缘已被海水磨得圆滑,不知是何年何月随波漂来的。
不同于现在,过去大多数时候,我去海边是为了干活。夏日里我得跟着母亲一起去自家的海蛎田,帮她把一根根青石条插进滩涂,顺便捡拾被浪打落的海蛎壳。等到了冬日,我又要踩着冰凉的海水,与母亲一同用长铁条撬削附在石上的海蛎,一不留神,锋利的贝壳边缘将手指割破,疼得人龇牙咧嘴。长大后,不再需要跟着母亲去海蛎田干活,我仍会不时跑去赶海,仿佛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有时情绪低落,对着大海吼叫几声,感觉烦恼也随海风飘远,恰如诗人胡仲弓写的《观海》:“海天云气入微茫,遥认潮头数点樯。眼界只消如许阔,不知何处是东洋。”人在海边,心胸自然开阔起来,烦恼也会在涛声中很快消融。
又一次站在故乡的海边,望着暮色里渐渐变成剪影的鲎屿,石头厝的残垣与岛屿相融,恍若巨鲎驮着老屋,缓缓向深海爬去。夕阳沉落,海风转凉,咸腥味更浓,我转身离开时,身后涛声依旧,潮涨潮落间,那些藏在记忆里的画面却愈发清晰——石屋的断梁、鲎甲的斑驳、伯父们当年凫水的背影,还有港口传来的汽笛声,都成了浅浅的潮痕,在记忆的滩涂上悄然浮现,也拼成故乡永不褪色的海色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