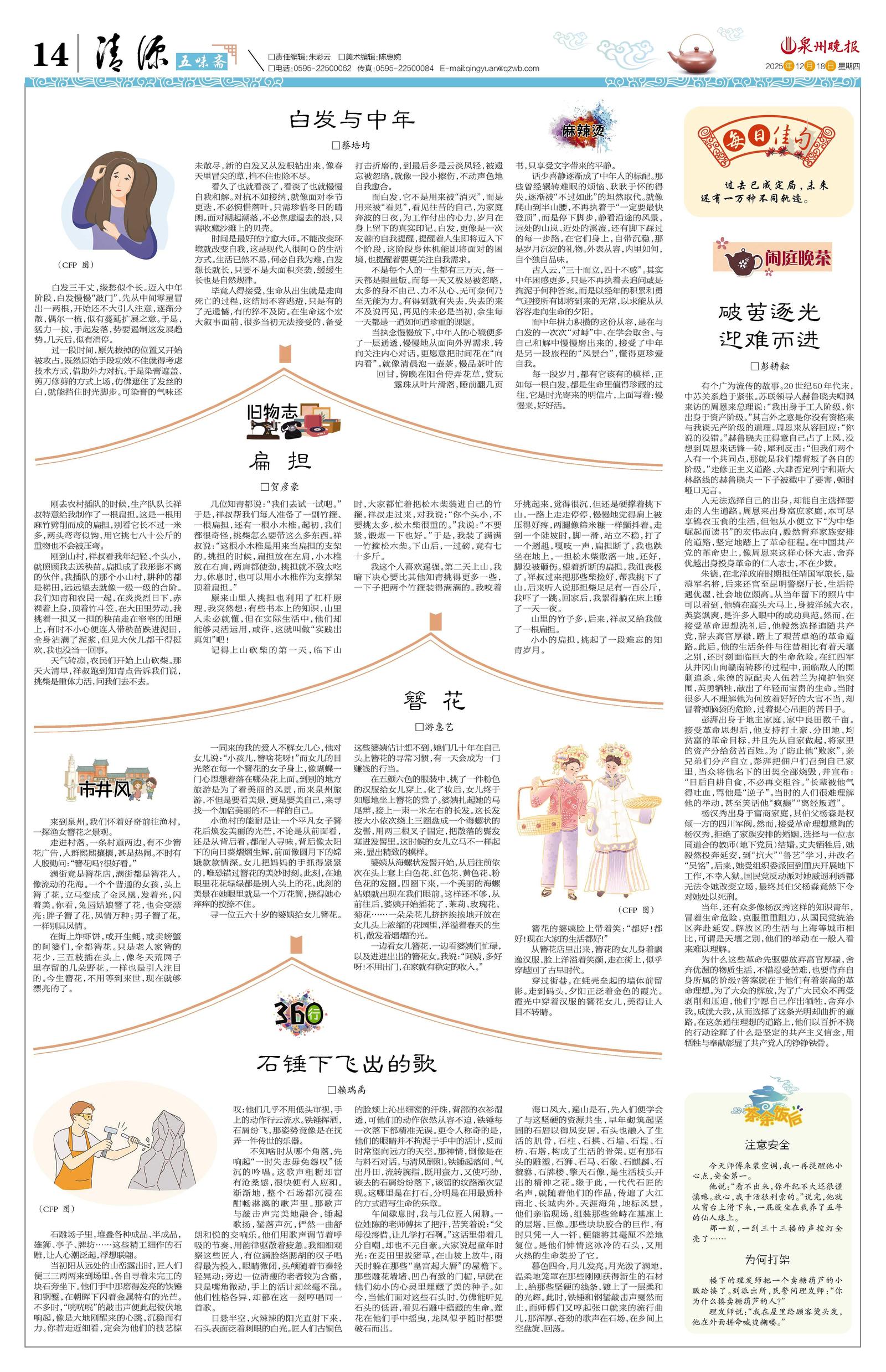石雕场子里,堆叠各种成品、半成品,雄狮、亭子、牌坊……这些精工细作的石雕,让人心潮泛起,浮想联翩。
当初阳从远处的山峦露出时,匠人们便三三两两来到场里,各自寻着未完工的块石旁坐下。他们手中那磨得发亮的铁锤和钢錾,在朝晖下闪着金属特有的光芒。不多时,“咣咣咣”的敲击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像是大地刚醒来的心跳,沉稳而有力。你若走近细看,定会为他们的技艺惊叹:他们几乎不用低头审视,手上的动作行云流水。铁锤挥洒,石屑纷飞,那姿势竟像是在抚弄一件传世的乐器。
不知啥时从哪个角落,先响起“一时失志毋免怨叹”低沉的吟唱。这歌声粗粝却富有沧桑感,很快便有人应和。渐渐地,整个石场都沉浸在酣畅淋漓的歌声里。那歌声与敲击声完美地融合,锤起歌扬,錾落声沉,俨然一曲舒朗和悦的交响乐。他们用歌声调节着呼吸的节奏,用韵律驱散着疲惫。我细细观察这些匠人,有位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唱得最为投入,眼睛微闭,头颅随着节奏轻轻晃动;旁边一位清瘦的老者较为含蓄,只是嘴角微动,手上的活计却丝毫不乱。他们性格各异,却都在这一刻哼唱同一首歌。
日悬半空,火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石头表面泛着刺眼的白光。匠人们古铜色的脸颊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背部的衣衫湿透,可他们的动作依然从容不迫,铁锤每一次落下都精准无误。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眼睛并不拘泥于手中的活计,反而时常望向远方的天空。那神情,倒像是在与料石对话,与清风酬和。铁锤起落间,气出丹田,流转腕指,既用蛮力,又使巧劲,该去的石屑纷纷落下,该留的纹路渐次显现。这哪里是在打石,分明是在用最质朴的方式谱写生命的乐章。
午间歇息时,我与几位匠人闲聊。一位姓陈的老师傅抹了把汗,苦笑着说:“父母没疼惜,让儿学打石啊。”这话里带着几分自嘲,却也不无自豪。大家说起童年时光:在麦田里拔猪草,在山坡上放牛,雨天时躲在那些“皇宫起大厝”的屋檐下。那些雕花墙堵、凹凸有致的门楣,早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藏了美的种子。如今,当他们面对这些石头时,仿佛能听见石头的低语,看见石雕中蕴藏的生命。莲花在他们手中摇曳,龙凤似乎随时都要破石而出。
海口风大,遍山是石,先人们便学会了与这坚硬的资源共生,早年砌筑起坚固的石厝以御风安居。石头也融入了生活的肌骨,石柱、石拱、石墙、石埕、石桥、石塔,构成了生活的骨架。更有那石头的雕塑,石狮、石马、石象、石麒麟、石貔貅、石牌楼、擎天石像,是生活枝头开出的精神之花。缘于此,一代代石匠的名声,就随着他们的作品,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涯海角,地标风景,他们亲临现场,组装那些耸峙在基座上的层塔、巨像。那些块块胶合的巨作,有时只凭一人一钎,便能将其毫厘不差地复位。是他们钟情这冰冷的石头,又用火热的生命装扮了它。
暮色四合,月儿发亮。月光泼了满地,温柔地笼罩在那些刚刚获得新生的石材上,给那些坚硬的线条,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辉。此时,铁锤和钢錾敲击声戛然而止,而师傅们又哼起张口就来的流行曲儿,那浑厚、苍劲的歌声在石场、在乡间上空盘旋、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