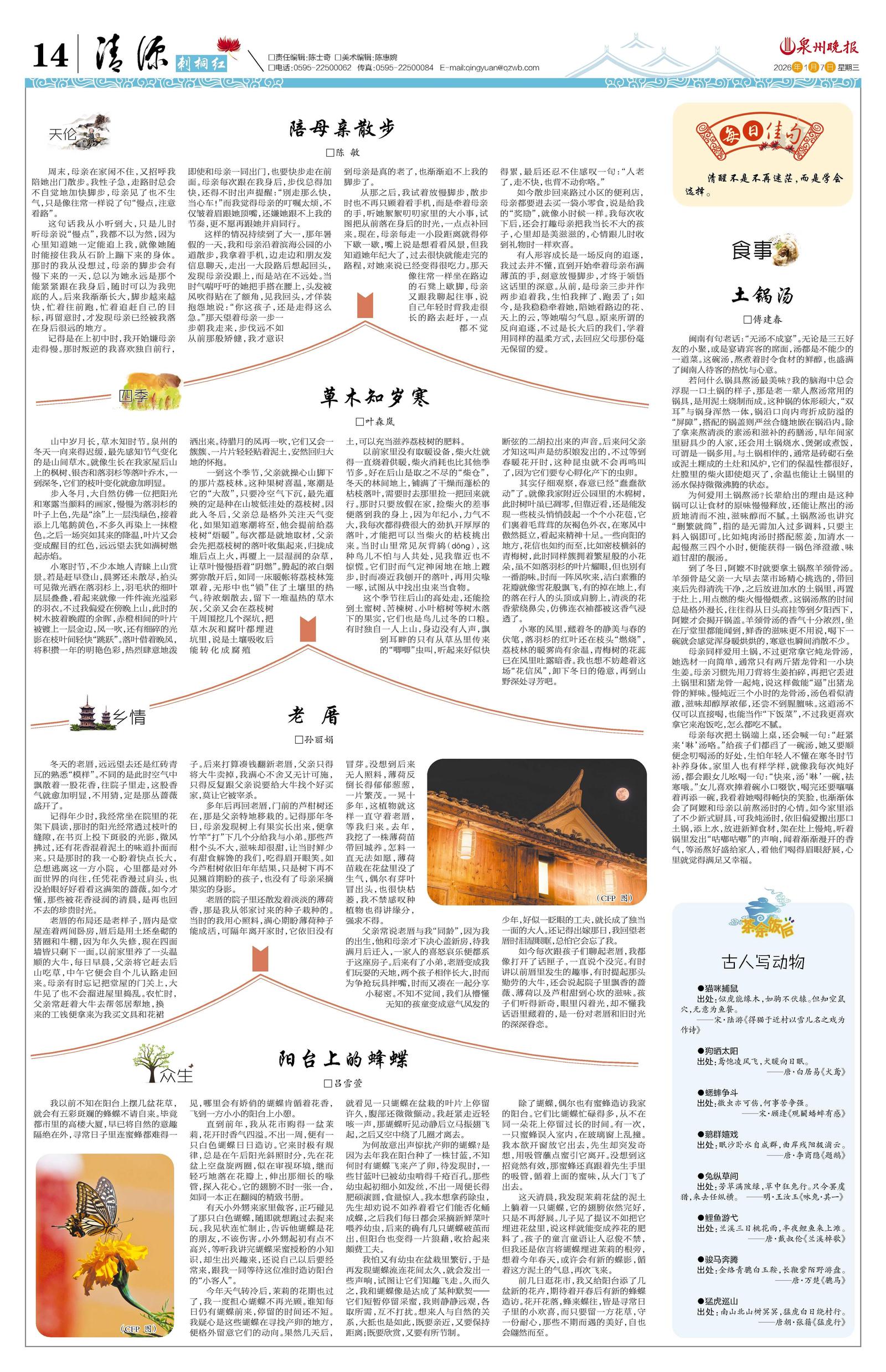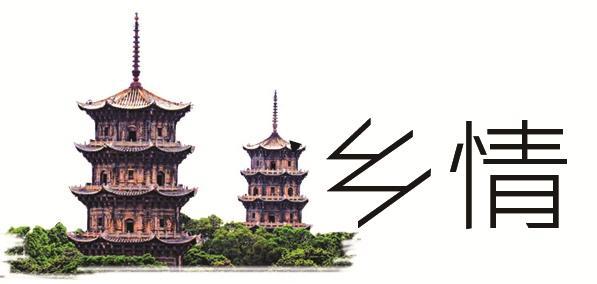冬天的老厝,远远望去还是红砖青瓦的熟悉“模样”。不同的是此时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花香,往院子里走,这股香气就愈加明显,不用猜,定是那丛蔷薇盛开了。
记得年少时,我经常坐在院里的花架下晨读,那时的阳光经常透过枝叶的缝隙,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微风拂过,还有花香混着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只是那时的我一心盼着快点长大,总想逃离这一方小院, 心里都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任凭花香漫过肩头,也没抬眼好好看看这满架的蔷薇。如今才懂,那些被花香浸润的清晨,是再也回不去的珍贵时光。
老厝的布局还是老样子,厝内是堂屋连着两间卧房,厝后是用土坯垒砌的猪圈和牛棚,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四面墙皆只剩下一面。以前家里养了一头温顺的大牛,每日早晨,父亲将它赶去后山吃草,中午它便会自个儿认路走回来。母亲有时忘记把堂屋的门关上,大牛见了也不会溜进屋里捣乱。农忙时,父亲常赶着大牛去帮邻居犁地,换来的工钱便拿来为我买文具和花裙子。后来打算凑钱翻新老厝,父亲只得将大牛卖掉,我满心不舍又无计可施,只得反复跟父亲说要给大牛找个好买家,莫让它被宰杀。
多年后再回老厝,门前的芦柑树还在,那是父亲特地移栽的。记得那年冬日,母亲发现树上有果实长出来,便拿竹竿“打”下几个分给我与小弟。那些芦柑个头不大,滋味却很甜,让当时鲜少有甜食解馋的我们,吃得眉开眼笑。如今芦柑树依旧年年结果,只是树下再不见翘首期盼的孩子,也没有了母亲采摘果实的身影。
老厝的院子里还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那是我从邻家讨来的种子栽种的。当时的我用心照料,满心期盼薄荷种子能成活,可隔年离开家时,它依旧没有冒芽。没想到后来无人照料,薄荷反倒长得郁郁葱葱,一片繁茂。一晃十多年,这植物就这样一直守着老厝,等我归来。去年,我挖了一株薄荷苗带回城养。怎料一直无法如愿,薄荷苗栽在花盆里没了生气,偶尔有芽叶冒出头,也很快枯萎,我不禁感叹种植物也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父亲常说老厝与我“同龄”,因为我的出生,他和母亲才下决心盖新房,待我满月后迁入,一家人的喜怒哀乐便都系于这座房子。后来有了小弟,老厝变成我们玩耍的天地,两个孩子相伴长大,时而为争抢玩具拌嘴,时而又凑在一起分享小秘密。不知不觉间,我们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变成意气风发的少年,好似一眨眼的工夫,就长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还记得出嫁那日,我回望老厝时泪湿眼眶,总怕它会忘了我。
如今每次跟孩子们聊起老厝,我都像打开了话匣子,一直说个没完。有时讲以前厝里发生的趣事,有时提起那头勤劳的大牛,还会说起院子里飘香的蔷薇、薄荷以及芦柑甜到心坎的滋味。孩子们听得新奇,眼里闪着光,却不懂我话语里藏着的,是一份对老厝和旧时光的深深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