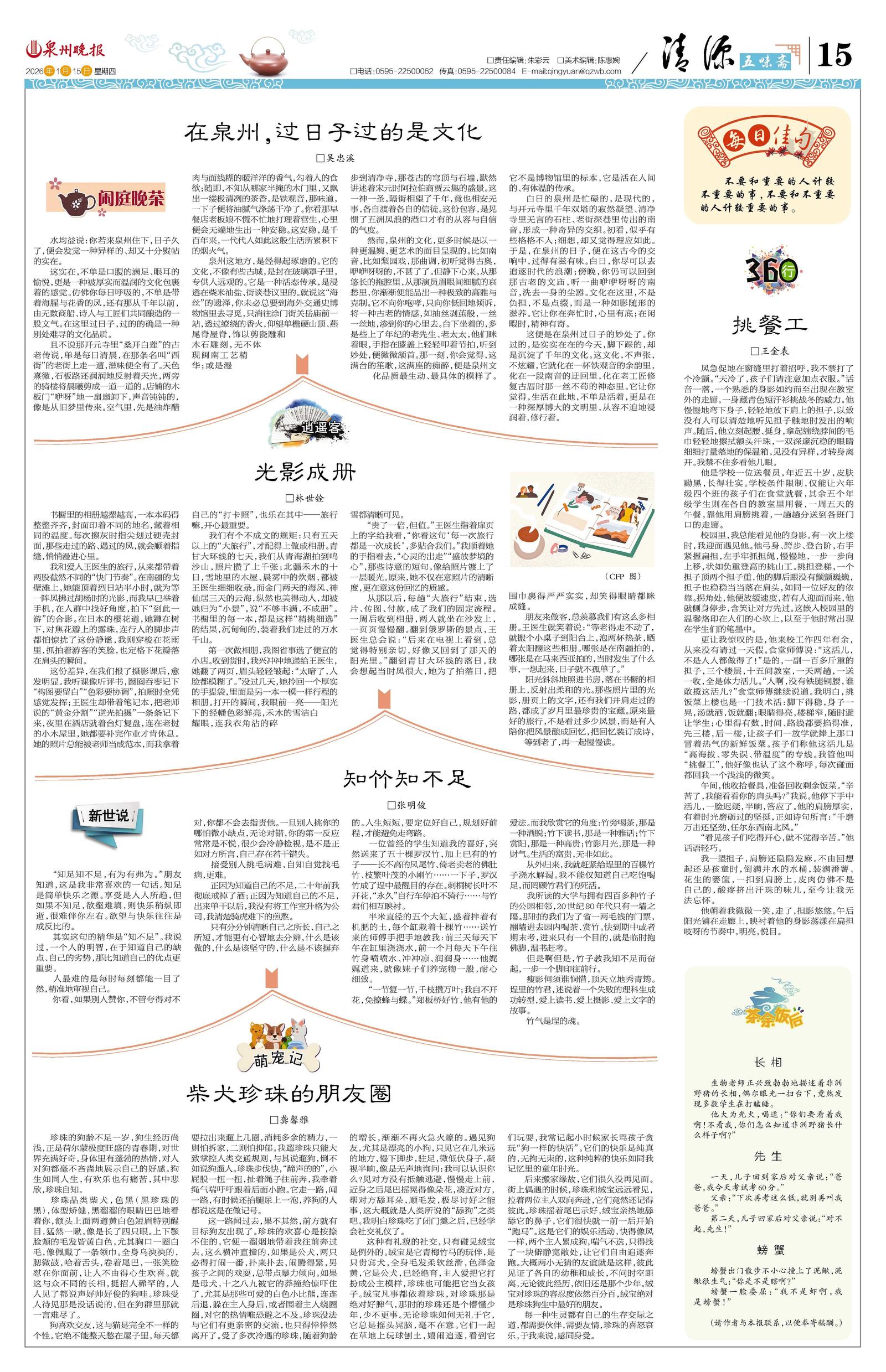书橱里的相册越摞越高,一本本码得整整齐齐,封面印着不同的地名,藏着相同的温度。每次擦灰时指尖划过硬壳封面,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风,就会顺着指缝,悄悄漫进心里。
我和爱人王医生的旅行,从来都带着两股截然不同的“快门节奏”。在南疆的戈壁滩上,她能顶着烈日站半小时,就为等一阵风拂过胡杨时的光影,而我早已举着手机,在人群中找好角度,拍下“到此一游”的合影。在日本的樱花道,她蹲在树下,对焦花瓣上的露珠,连行人的脚步声都怕惊扰了这份静谧,我则穿梭在花雨里,抓拍着游客的笑脸,也定格下花瓣落在肩头的瞬间。
这份差异,在我们报了摄影课后,愈发明显。我听课像听评书,囫囵吞枣记下“构图要留白”“色彩要协调”,拍照时全凭感觉发挥;王医生却带着笔记本,把老师说的“黄金分割”“逆光拍摄”一条条记下来,夜里在酒店就着台灯复盘,连在老挝的小木屋里,她都要补完作业才肯休息。她的照片总能被老师当成范本,而我拿着自己的“打卡照”,也乐在其中——旅行嘛,开心最重要。
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有五天以上的“大旅行”,才配得上做成相册。青甘大环线的七天,我们从青海湖拍到鸣沙山,照片攒了上千张;北疆禾木的十日,雪地里的木屋、晨雾中的炊烟,都被王医生细细收录。而金门两天的海风、神仙居三天的云海,纵然也美得动人,却被她归为“小景”,说“不够丰满,不成册”。书橱里的每一本,都是这样“精挑细选”的结果,沉甸甸的,装着我们走过的万水千山。
第一次做相册,我图省事选了便宜的小店。收到货时,我兴冲冲地递给王医生,她翻了两页,眉头轻轻皱起:“太暗了,人脸都模糊了。”没过几天,她拎回一个厚实的手提袋,里面是另一本一模一样行程的相册。打开的瞬间,我眼前一亮——阳光下的经幡色彩鲜亮,禾木的雪洁白耀眼,连我衣角沾的碎雪都清晰可见。
“贵了一倍,但值。”王医生指着扉页上的字给我看,“你看这句‘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成长’,多贴合我们。”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心灵的出走”“盛放梦境的心”,那些诗意的短句,像给照片镀上了一层暖光。原来,她不仅在意照片的清晰度,更在意这份回忆的质感。
从那以后,每趟“大旅行”结束,选片、传图、付款,成了我们的固定流程。一周后收到相册,两人就坐在沙发上,一页页慢慢翻。翻到俄罗斯的景点,王医生总会说:“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总觉得特别亲切,好像又回到了那天的阳光里。”翻到青甘大环线的落日,我会想起当时风很大,她为了拍落日,把围巾裹得严严实实,却笑得眼睛都眯成缝。
朋友来做客,总羡慕我们有这么多相册。王医生就笑着说:“等老得走不动了,就搬个小桌子到阳台上,泡两杯热茶,晒着太阳翻这些相册。哪张是在南疆拍的,哪张是在马来西亚拍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来,日子就不孤单了。”
阳光斜斜地照进书房,落在书橱的相册上,反射出柔和的光。那些照片里的光影,册页上的文字,还有我们并肩走过的路,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看过多少风景,而是有人陪你把风景酿成回忆,把回忆装订成诗,等到老了,再一起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