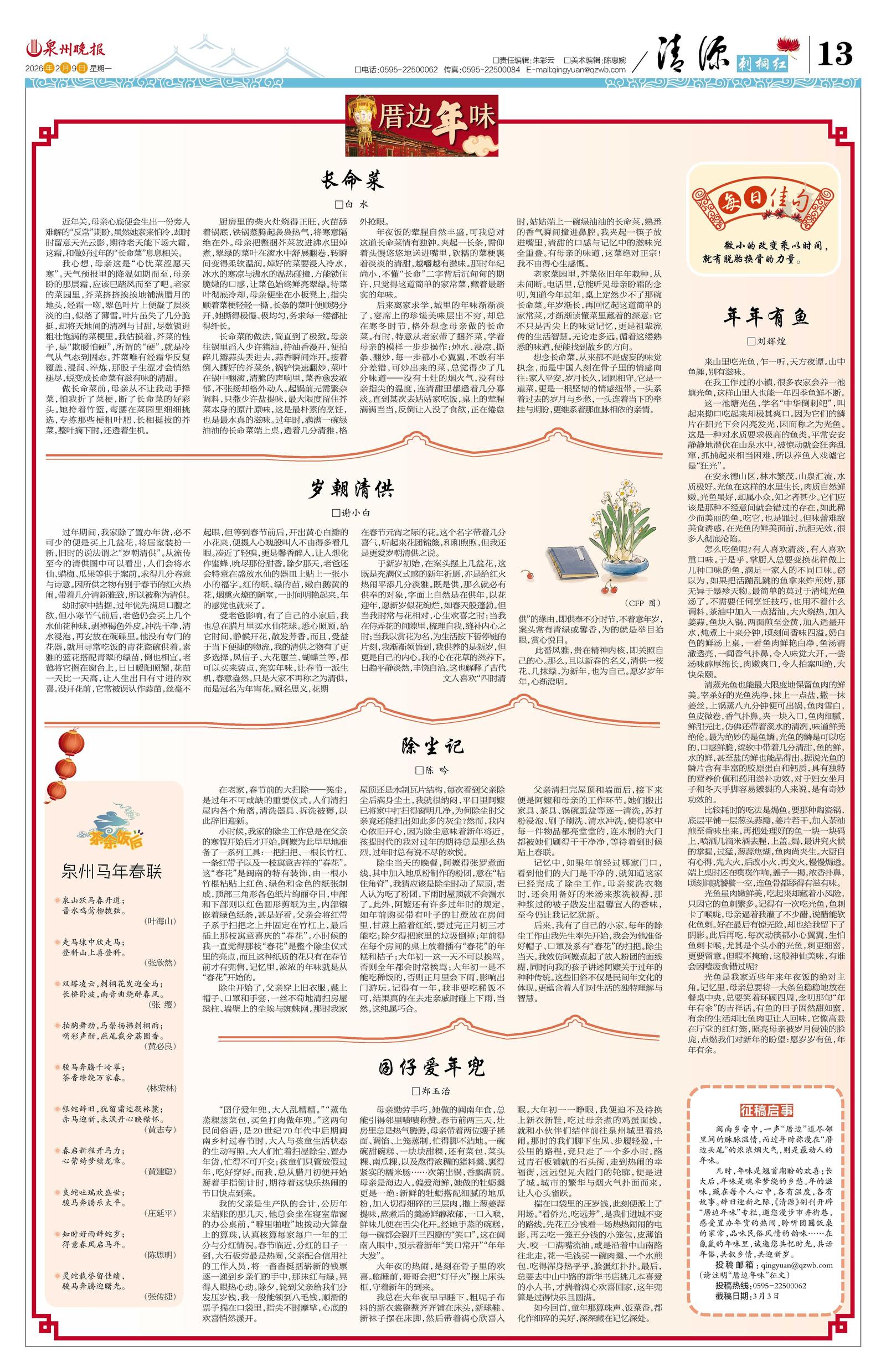近年关,母亲心底便会生出一份旁人难解的“反常”期盼。虽然她素来怕冷,却时时留意天光云影,期待老天能下场大霜,这霜,和做好过年的“长命菜”息息相关。
我心想,母亲这是“心忧菜涩愿天寒”。天气预报里的降温如期而至,母亲盼的那层霜,应该已踏风而至了吧。老家的菜园里,芥菜挤挤挨挨地铺满腊月的地头,经霜一吻,翠色叶片上便凝了层淡淡的白,似落了薄雪。叶片虽失了几分脆挺,却将天地间的清冽与甘甜,尽数锁进粗壮饱满的菜梗里。我估摸着,芥菜的性子,是“欺暖怕硬”,所谓的“硬”,就是冷气从气态到固态。芥菜唯有经霜华反复覆盖、浸润、淬炼,那股子生涩才会悄然褪尽,蜕变成长命菜有滋有味的清甜。
做长命菜前,母亲从不让我动手择菜,怕我折了菜梗,断了长命菜的好彩头。她挎着竹篮,弯腰在菜园里细细挑选,专拣那些梗粗叶肥、长相挺拔的芥菜,整叶摘下时,还透着生机。
厨房里的柴火灶烧得正旺,火苗舔着锅底,铁锅蒸腾起袅袅热气,将寒意隔绝在外。母亲把整捆芥菜放进沸水里焯煮,翠绿的菜叶在滚水中舒展翻卷,转瞬间变得柔软温润。焯好的菜要浸入冷水,冰水的寒凉与沸水的温热碰撞,方能锁住脆嫩的口感,让菜色始终鲜亮翠绿。待菜叶彻底冷却,母亲便坐在小板凳上,指尖顺着菜梗轻轻一撕,长条的菜叶便顺势分开,她撕得极慢、极均匀,务求每一缕都扯得纤长。
长命菜的做法,简直到了极致。母亲往锅里舀入少许猪油,待油香漫开,便拍碎几瓣蒜头丢进去,蒜香瞬间炸开。接着倒入撕好的芥菜条,锅铲快速翻炒,菜叶在锅中翻滚,清脆的声响里,菜香愈发浓郁,不张扬却格外动人。起锅前无需繁杂调料,只撒少许盐提味,最大限度留住芥菜本身的原汁原味,这是最朴素的烹饪,也是最本真的滋味。过年时,满满一碗绿油油的长命菜端上桌,透着几分清雅,格外抢眼。
年夜饭的荤腥自然丰盛,可我总对这道长命菜情有独钟。夹起一长条,需仰着头慢悠悠地送进嘴里,软糯的菜梗裹着淡淡的清甜,越嚼越有滋味。那时年纪尚小,不懂“长命”二字背后沉甸甸的期许,只觉得这道简单的家常菜,藏着最踏实的年味。
后来离家求学,城里的年味渐渐淡了,宴席上的珍馐美味层出不穷,却总在寒冬时节,格外想念母亲做的长命菜。有时,特意从老家带了捆芥菜,学着母亲的模样一步步操作:焯水、浸凉、撕条、翻炒,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敢有半分差错,可炒出来的菜,总觉得少了几分味道——没有土灶的烟火气,没有母亲指尖的温度,连清甜里都透着几分寡淡。直到某次去姑姑家吃饭,桌上的荤腥满满当当,反倒让人没了食欲,正在倦怠时,姑姑端上一碗绿油油的长命菜,熟悉的香气瞬间撞进鼻腔。我夹起一筷子放进嘴里,清甜的口感与记忆中的滋味完全重叠。有母亲的味道,这菜绝对正宗!我不由得心生感慨。
老家菜园里,芥菜依旧年年栽种,从未间断。电话里,总能听见母亲盼霜的念叨,知道今年过年,桌上定然少不了那碗长命菜。年岁渐长,再回忆起这道简单的家常菜,才渐渐读懂菜里藏着的深意:它不只是舌尖上的味觉记忆,更是祖辈流传的生活智慧。无论走多远,循着这缕熟悉的味道,便能找到故乡的方向。
想念长命菜,从来都不是虚妄的味觉执念,而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感向往:家人平安,岁月长久,团圆相守。它是一道菜,更是一根坚韧的情感纽带,一头系着过去的岁月与乡愁,一头连着当下的牵挂与期盼,更维系着那血脉相依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