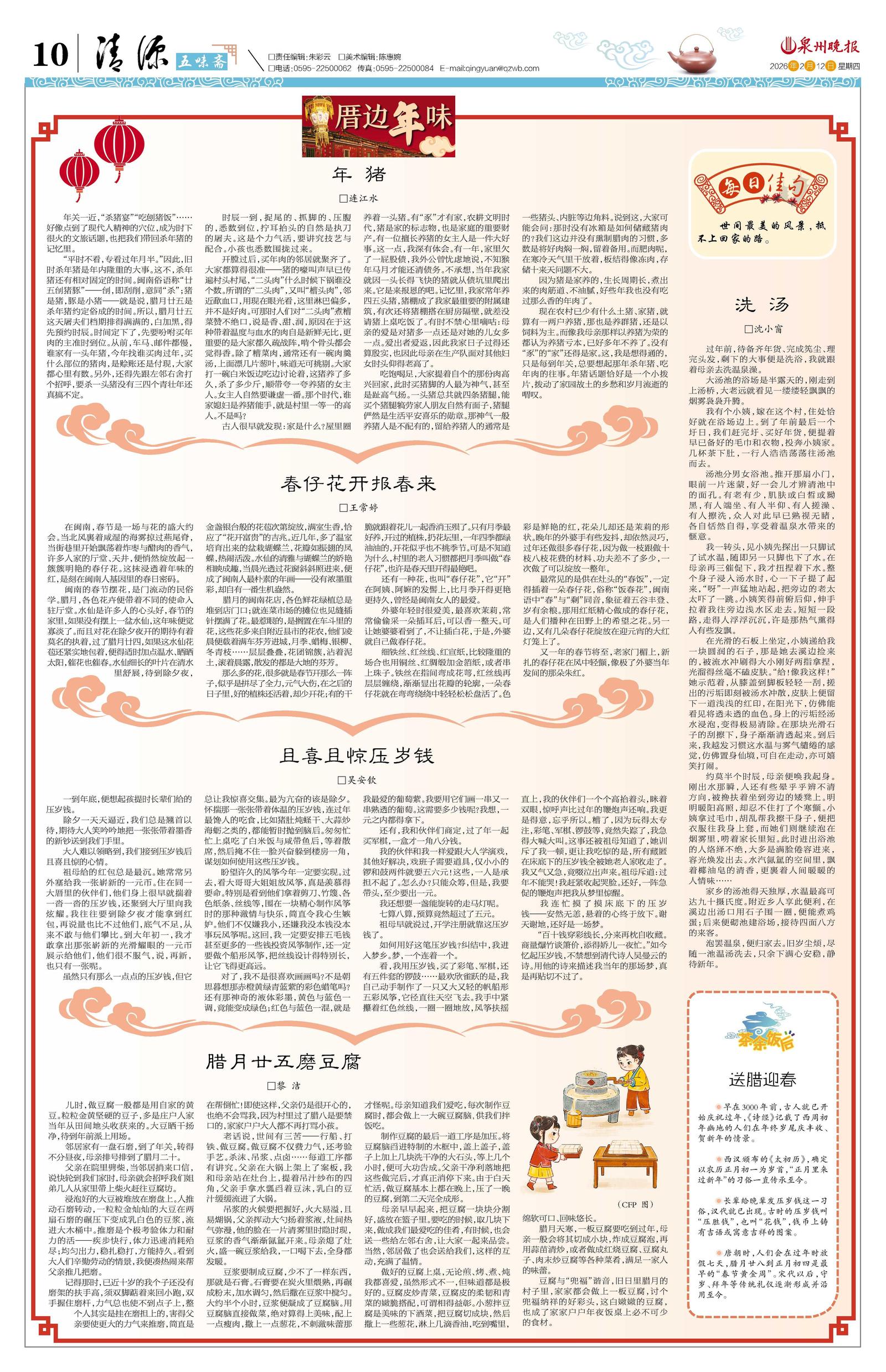□连江水
年关一近,“杀猪宴”“吃刨猪饭”……好像点到了现代人精神的穴位,成为时下很火的文旅话题,也把我们带回杀年猪的记忆里。
“平时不看,专看过年月半。”因此,旧时杀年猪是年内隆重的大事。这不,杀年猪还有相对固定的时间。闽南俗语称“廿五刣猪豚”——刣,即刮削,意同“杀”;猪是猪,豚是小猪——就是说,腊月廿五是杀年猪约定俗成的时间。所以,腊月廿五这天屠夫们档期排得满满的,白加黑,得先预约时辰。时间定下了,先要吩咐买年肉的主准时到位。从前,车马、邮件都慢,谁家有一头年猪,今年找谁买肉过年,买什么部位的猪肉,是赊账还是付现,大家都心里有数。另外,还得先跟左邻右舍打个招呼,要杀一头猪没有三四个青壮年还真搞不定。
时辰一到,捉尾的、抓脚的、压腹的,悉数到位,拧耳抬头的自然是执刀的屠夫。这是个力气活,要讲究技艺与配合。小孩也悉数围拢过来。
开膛过后,买年肉的邻居就聚齐了。大家都算得很准——猪的嚎叫声早已传遍村头村尾,“二头肉”什么时候下锅谁没个数。所谓的“二头肉”,又叫“槽头肉”,邻近歃血口,用现在眼光看,这里淋巴偏多,并不是好肉。可那时人们对“二头肉”煮糟菜赞不绝口,说是香、甜、润,原因在于这种带着温度与血水的肉自是新鲜无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久疏战阵,啃个骨头都会觉得香。除了糟菜肉,通常还有一碗肉羹汤,上面漂几片葱叶,味道无可挑剔。大家打一碗白米饭边吃边讨论着,这猪养了多久,杀了多少斤,顺带夸一夸养猪的女主人。女主人自然要谦虚一番。那个时代,谁家媳妇是养猪能手,就是村里一等一的高人。不是吗?
古人很早就发现:家是什么?屋里圈养着一头猪。有“豕”才有家,农耕文明时代,猪是家的标志物,也是家庭的重要财产。有一位擅长养猪的女主人是一件大好事。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有一年,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我外公曾忧虑地说,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债务。不承想,当年我家就因一头长得飞快的猪就从债坑里爬出来。它是来报恩的吧。记忆里,我家常年养四五头猪,猪棚成了我家最重要的附属建筑,有次还将猪棚搭在厨房隔壁,就差没请猪上桌吃饭了。有时不禁心里嘀咕:母亲的爱是对猪多一点还是对她的儿女多一点。爱出者爱返,因此我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也因此母亲在生产队面对其他妇女时头仰得老高了。
吃饱喝足,大家提着自个的那份肉高兴回家,此时买猪脚的人最为神气,甚至是趾高气扬。一头猪总共就四条猪腿,能买个猪腿犒劳家人朋友自然有面子,猪腿俨然是生活平安喜乐的勋章。那神气一般养猪人是不配有的,留给养猪人的通常是一些猪头、内脏等边角料。说到这,大家可能会问:那时没有冰箱是如何储藏猪肉的?我们这边并没有熏制腊肉的习惯,多数是将好肉焖一焖,留着备用。而肥肉呢,在寒冷天气里干放着,板结得像冻肉,存储十来天问题不大。
因为猪是家养的,生长周期长,煮出来的肉筋道、不油腻,好些年我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年肉了。
现在农村已少有什么土猪、家猪,就算有一两户养猪,那也是养群猪,还是以饲料为主。而像我母亲那样以养猪为荣的都认为养猪亏本,已好多年不养了。没有“豕”的“家”还得是家。这,我是想得通的,只是每到年关,总要想起那年杀年猪、吃年肉的往事。年猪话题恰好是一个小拨片,拨动了家园故土的乡愁和岁月流逝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