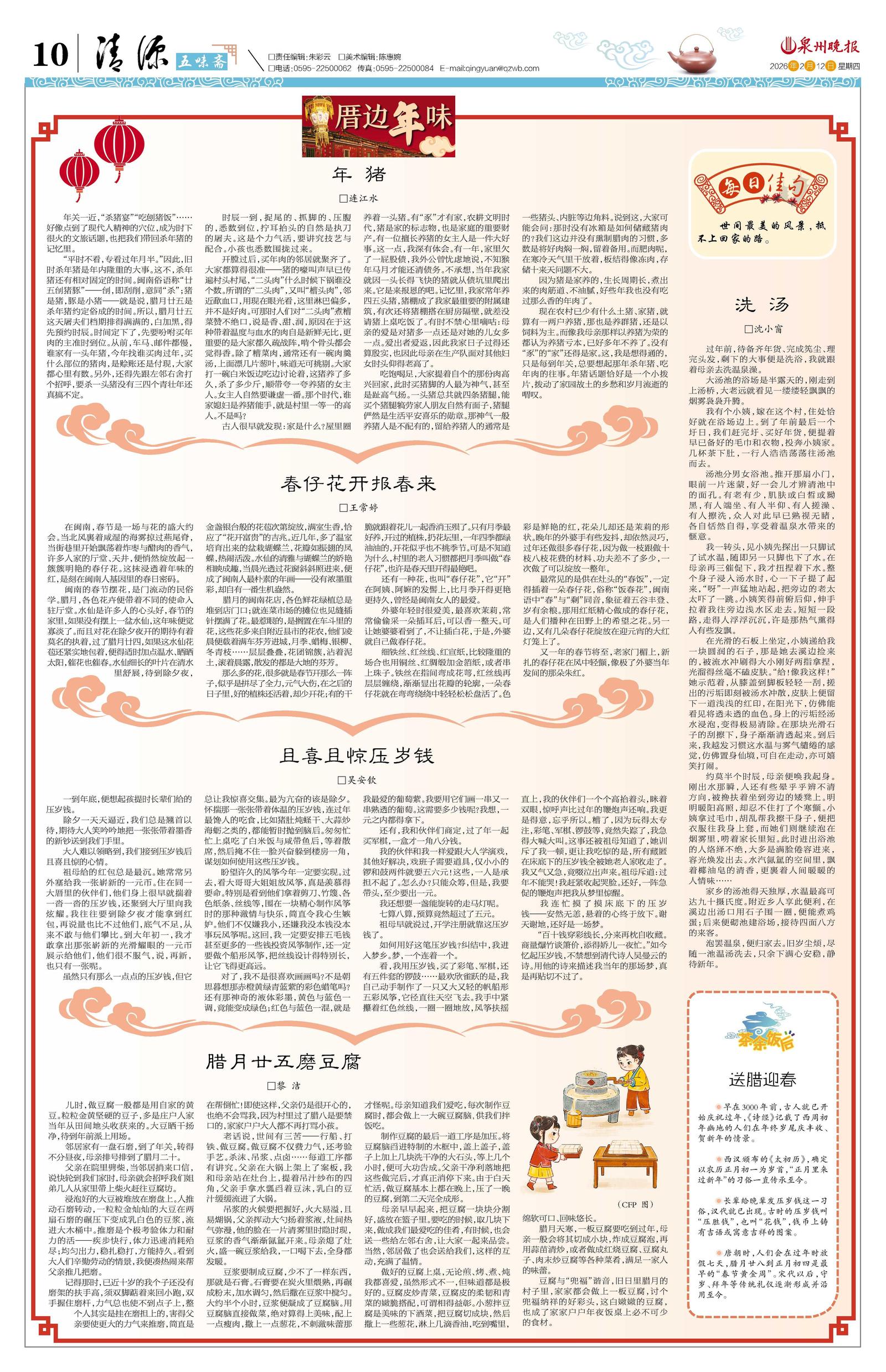□黎 洁
儿时,做豆腐一般都是用自家的黄豆。粒粒金黄坚硬的豆子,多是庄户人家当年从田间地头收获来的。大豆晒干扬净,待到年前派上用场。
邻居家有一盘石磨,到了年关,转得不分昼夜,母亲排号排到了腊月二十。
父亲在院里劈柴,当邻居捎来口信,说快轮到我们家时,母亲就会招呼我们姐弟几人从家里带上柴火赶往豆腐坊。
浸泡好的大豆被堆放在磨盘上。人推动石磨转动,一粒粒金灿灿的大豆在两扇石磨的碾压下变成乳白色的豆浆,流进大木桶中。推磨是个极考验体力和耐力的活——疾步快行,体力迅速消耗殆尽;均匀出力,稳扎稳打,方能持久。看到大人们辛勤劳动的情景,我便凑热闹来帮父亲推几把磨。
记得那时,已近十岁的我个子还没有磨架的扶手高,须双脚踮着来回小跑,双手握住磨杆,力气总也使不到点子上,整个人其实是挂在磨担上的,害得父亲要使更大的力气来推磨,简直是在帮倒忙!即使这样,父亲仍是很开心的,也绝不会骂我,因为村里过了腊八是要禁口的,家家户户大人都不再打骂小孩。
老话说,世间有三苦——行船、打铁、做豆腐。做豆腐不仅费力气,还考验手艺。杀沫、吊浆、点卤……每道工序都有讲究。父亲在大锅上架上了案板,我和母亲站在灶台上,提着吊汁纱布的四角,父亲手拿水瓢舀着豆沫,乳白的豆汁缓缓流进了大锅。
吊浆的火候要把握好,火大易溢,且易煳锅,父亲挥动大勺扬着浆液,灶间热气弥漫,他的脸在一片清雾里时隐时现,豆浆的香气渐渐氤氲开来。母亲熄了灶火,盛一碗豆浆给我,一口喝下去,全身都发暖。
豆浆要制成豆腐,少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石膏。石膏要在炭火里煨熟,再碾成粉末,加水调匀,然后撒在豆浆中搅匀。大约半个小时,豆浆便凝成了豆腐脑。用豆腐脑直接做菜,绝对算得上美味,配上一点瘦肉,撒上一点葱花,不刺激味蕾那才怪呢。母亲知道我们爱吃,每次制作豆腐时,都会做上一大碗豆腐脑,供我们拌饭吃。
制作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加压。将豆腐脑舀进特制的木框中,盖上盖子,盖子上加上几块洗干净的大石头,等上几个小时,便可大功告成。父亲干净利落地把这些做完后,才真正消停下来。由于白天忙活,做豆腐基本上都在晚上,压了一晚的豆腐,到第二天完全成形。
母亲早早起来,把豆腐一块块分割好,盛放在篮子里。要吃的时候,取几块下来,做成我们最爱吃的佳肴,有时候,也会送一些给左邻右舍,让大家一起来品尝。当然,邻居做了也会送给我们,这样的互动,充满了温情。
做好的豆腐上桌,无论煎、烤、煮、炖我都喜爱,虽然形式不一,但味道都是极好的。豆腐皮炒青菜,豆腐皮的柔韧和青菜的嫩脆搭配,可谓相得益彰。小葱拌豆腐是美味的下酒菜,把豆腐切成块,然后撒上一些葱花,淋上几滴香油,吃到嘴里,绵软可口、回味悠长。
腊月天寒,一板豆腐要吃到过年,母亲一般会将其切成小块,炸成豆腐泡,再用蒜苗清炒,或者做成红烧豆腐、豆腐丸子、肉末炒豆腐等各种菜肴,满足一家人的味蕾。
豆腐与“兜福”谐音,旧日里腊月的村子里,家家都会做上一板豆腐,讨个兜福纳祥的好彩头,这白嫩嫩的豆腐,也成了家家户户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